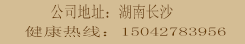![]() 当前位置: 斑胸草雀 > 斑胸草雀的形状 > 宝拍中国古代故事镜图集上
当前位置: 斑胸草雀 > 斑胸草雀的形状 > 宝拍中国古代故事镜图集上

![]() 当前位置: 斑胸草雀 > 斑胸草雀的形状 > 宝拍中国古代故事镜图集上
当前位置: 斑胸草雀 > 斑胸草雀的形状 > 宝拍中国古代故事镜图集上
在中国铜镜四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华夏先人创造了太多奇幻瑰丽、恢诡谲怪、或抽象,或写实的铜镜纹饰造型。铜镜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多样化的风貌正是一个时期科技、文化、人文、风俗,宗教的直观呈现。沈从文曾言:“我们可以从不同形制和图案花纹的发展中,看出镜子对于社会现实的种种不同反映,和社会上层建筑中的文学、诗歌、音乐、美术、及宗教信仰的种种联系。”可以说,铜镜装饰艺术是古代文明与人文信息的载体,一面铜镜便是一段凝固的历史。
在众多的铜镜装饰主题中,有一类以刻画故事场景或具情节化设定图景为主题的铜镜类型,多称为故事镜。故事镜指镜背装饰纹样为特定场景的一个固化状态,是对于场景或情节的描绘,而非对单一物的描写,可以来源于民间流行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或体现场景的高山流水、苍树老翁、云烟楼阁等等。能够切实反应儒、释、道等诸家思想的精神追求,反应当时社会文化和风尚的诸多问题,并能寄托情感,引人深思及鉴赏。故事镜的出现伴随着写实艺术在装饰艺术的发展,在神诡的抽象艺术并不能完全满足人们对于美的要求的情况下,写实艺术,以具化事物的手法,且具情节化的设定,在铜镜装饰纹样方面开启的新的篇章。
中国古代故事镜依其镜背的文化属性大致可以分为四类,首先是神话传说类故事镜,此类镜的特点是带有明显的佛道宗教色彩,或是来源于民间与古籍记载的神话传说、或是体现道家升仙的修炼法门亦或是描绘神仙世界来表达祈福的愿望;第二类是为先贤典故类故事镜,此类镜的主题来源多为历史典故,或描绘高士隐居场景的图式,其风格有着较为明显寓教作用,并能寄托现世情感与思想文化,是儒释道哲学思想最直观的表达;第三类为民俗文化类故事镜,此类镜的装饰主题有着极明显的时代特征,是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市井文化与人文风俗的直观呈现;第四类是绘画类故事镜,是唐宋时期空前发达的文人绘画艺术在铜镜装饰艺术的体现,其纹样大多没有明显的传说或典故来源,较为典型的是描绘仕女观景的图式与写意花鸟山水的图式。
古代故事镜是文人绘画与铜镜美学融合的天成之作,仿似以青铜铸制的画卷,其造诣在于意境的呈现。仕女自画像镜直观的展现出“每座台前见玉容,今朝不与昨朝同。良人一夜出门去,减却桃花一半红。”的闺怨;观许由巢父镜,可以领悟“薄世临流洗耳尘,便归云洞任天真。一瓢风入犹嫌闹,何况人间万种人。”的洒脱心境;赏王质观棋镜,可感受“世事由来一局棋,千秋得失几人知。直从弹指观无著,翻笑柯仙领悟迟。”的时间观念;赏镜亦如赏画,其美在“艺”更在于“道”,每面故事镜都充实着创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所以更强调意境与神韵,可谓是文人艺术与科技工艺的造极之物。
错金银狩猎纹镜
民国时期洛阳金村大墓出土的战国错金银斗兽纹铜镜,残存鎏金,镜面高锡也与镜背不同,珍贵的复合镜。半环钮,外饰凹面宽带一周,外侧弦纹圈接等距饰三片银色扁叶纹,间以六组错金银纹饰。其中以上方骑士搏虎图最为特殊,只见勇士鹖冠披甲,蹲在战马之上,左手执缰,右手持剑欲刺猛虎,左侧斑纹猛虎也不甘示弱,作欲噬状态,场面激烈。
武士斗兽镜
此镜纹饰由地纹与主纹构成,地纹由三角云雷纹组成的勾连山字纹及排列紧密有序的圆珠纹结合而成。主纹饰由两组斗兽纹绕钮排列,双武士分别左手持盾,右手握剑,面对虎豹作搏斗状,其豹张口嘶鸣,作飞扑状;其虎回首坐立,呈惊恐状。全镜制作精良,工艺巅峰精湛,是战国时期秦国青铜镜中存世极罕的大珍品。其余两面分别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日本兵库县立考古博物馆藏。
平螺钿高士宴乐镜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螺钿镜是盛唐独有的特种工艺镜精品,堪称中国铜镜史上的巅峰之作。《髹饰录》文曰:“螺钿,一名甸嵌,一名陷蚌,一名坎螺,即螺填也。百般文图,点、抹、钩、条,总以精细密致如画为妙。又分截壳色,随彩而施缀者,光华可赏。又有片嵌者,界郭理皴皆以划文。”具有“天机织贝,冰蚕失文”之美,又称“霞锦”。现存螺细镜共有19面,皆为盛唐所造:国内唐皇室贵胄墓出土7面,日本千石唯司、白鹤美术馆和美国不列颠博物馆藏各藏1面,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传世9面,均为遣唐使带回的大唐“国礼”。
月宫镜
月宫镜镜背图式为广寒仙府的月宫图景,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取材于民间经典的神仙传说“嫦娥奔月”,刘安《淮南子.览冥训》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托与姮娥。逢蒙往而窃之,窃之不成,欲加害姮娥。娥无以为计,吞不死药以升天。然不忍离羿而去,滞留月宫。广寒寂寥,怅然有丧,无以继之,遂催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欲配飞升之药,重回人间焉。”,李商隐诗作《嫦娥》:“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白诗作《把酒问月》:“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此时社会关于月宫图式与嫦娥形象已经较为详细,嫦娥、玉兔、神药,桂树等是月宫的主要元素,甚至在社会文化中已成为月宫的代名词。月宫镜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不仅道家升仙文化在社会的盛行,代表了人们对于神仙世界的向往,同时通过对嫦娥凄婉形象的描绘,有折射出恋人分别,天上人间的相思之意。
三乐镜
三乐的故事见于《列子天瑞》:“孔子游于泰山,见荣启奇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
打马球镜
打马球,古称“击鞠”,是一种骑马用长柄球槌击打木球的运动。这项运动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流行于中原地区,三国曹植《名都篇》中即有“连翩击鞠壤”之句。到了唐代,打马球绝对是当时影响最广、声势最大的运动项目,并在有唐一代三百年间盛行不衰。不仅皇室、军队盛行,就连文人学士、宫女妓妾,皆习此技。由于马球运动在唐代风靡一时,修筑球场亦蔚然成风。年,西安北郊唐大明宫遗址范围内出土一块方形石碑,上刻“含光殿及球场等大唐大和辛亥岁己未月建”,将球场与宫殿并提,足见对马球的重视程度。
狩猎纹镜
唐代,狩猎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火攻、围猎、网捕、索套、骑马箭射等,有时是几种结合在一起。这点我们可以从唐代铜镜上猎纹可以看出,当时的狩猎方式多为骑马射猎,弓箭是常用的狩猎工具。猎者跃马,驰骋于草木林间,或挽弓欲射,或箭已离弦。场上的动物惊慌失措,四下逃窜。狩猎的情景非常紧张,扣人心弦。
洞天道隐故事镜
此镜为高士隐逸的图景化呈现,镜背以浮雕技法铸饰高山流水,古木葱茂,草屋人家,场景刻画精妙,山石嶙峋,流水潺潺,一幅淡泊清幽的气韵,茅屋之下一高士端坐,符合古代文人对于隐逸生活的向往。
真子飞霜镜
“真子飞霜"镜流行于唐代,但对于“真子飞霜"铜镜画面上所体现的故事,则众说不一。有观点认为真子飞霜镜讲述的是天子抚琴,凤凰来仪,舜死于苍梧之野的故事。亦有观点认为真子为人名,飞霜为所弹之曲名《履霜操》的别称。还有观点认为,“真子飞霜"镜的纹饰,反映了唐代道教飞仙长生思想的流行,是道教思想在唐代盛行的反映。
王子乔吹笙引凤镜
此镜取材于“王子乔吹笙引凤”的神话传说,汉代刘向《列仙传》记载:“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柏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鹤驻山头,望之不可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王子乔是东周时周灵王的太子,天资灵颖,温良博学。时遇水患,周灵王准备用壅堵的办法治理,遭到太子晋强烈反对,并直言进谏,不料被废黜为庶人。他内心郁郁,出游于伊、洛水间,随道士浮丘公上嵩山,三十年后得到乘鹤成仙。
高逸镜
此镜以意趣淡雅的高逸图为饰,铸造精美,构思精妙,纹饰以平雕技法刻画,工艺精湛。镜背布局紧凑,分为三组图式:黄帝问道、许由巢父与商山四皓,是唐时隐逸思想的直观呈现。
竹林七贤镜
唐代七贤镜难得一见,此镜寓意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乃三国魏时嵇康、阮籍等七贤人,他们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酐畅。
宫廷宴乐镜
董永孝义故事镜
相传董永为东汉时期千乘(今山东高青县北)人,少年丧母,因避兵乱迁居安陆(今属湖北)。其后父亲亡故,董永卖身至一富家为奴,换取丧葬费用。上工路上,于槐荫下遇一女子,自言无家可归,二人结为夫妇。女子以一月时间织成三百匹锦缎,为董永抵债赎身,返家途中,行至槐荫,女子告诉董永:自己是天帝之女,奉命帮助董永还债。言毕凌空而去。因此,槐荫改名为孝感。
医圣孙思邈降龙伏虎镜
此镜纹饰内容有着极强的道家风格,这与宋金时期道家思想的流行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连年战争,社会动荡,百姓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无奈改变现实生活的条件下,人们就将这种情感的希冀寄托在神仙道法之上,希望通过律己修仙改变命运,道家各派得以迅速发展至鼎盛时期,此时道家长生不死的思想深入人心,渗透在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种社会风尚的影响下,铜镜上出现了众多体现道家思想的纹饰,均以故事场景的固化状态呈现,多取材于民间流传的道家典故与宣扬道法高深的降妖捉鬼场景,其中一类以刻画炼丹场景及方法,体现道家内丹学的题材尤为特殊,如此镜,不仅是对于道家仙法的刻画,同样也反映出修炼内丹的诸多内容。
降龙伏虎镜
仕女自画像镜
每坐台前见玉容,今朝不与昨朝同。
良人一夜出门宿,减却桃花一半红。
明代薛姬对镜自画像《中国历代仕女图集》
二仙渡海镜
纹饰图景呈现出强烈的道家文化气息,整镜满铺细密的海水纹,水波细密,曲折起伏,浪花翻涌,一幅波澜壮阔的即视感。镜钮右侧饰有一仙人踏剑飞行,头梳髽髻,神情淡然,身着宽袍,衣纹流畅,衣袂飘遥,一派道骨仙风,超凡出尘,御剑飞行于无边海域;左侧海龙出水吐息,镜钮下方水波之中鱼纹若隐若现,场景刻画极为精妙。
南宋吕洞宾渡海图
吕洞宾渡海镜
婴戏蹴鞠纹镜
“婴戏”题材为这一时期较为经典的一个艺术主题,且应用颇广,最早即被具有独特艺术气息的文人雅士所捕捉并运用在绘画艺术上,因其体现了对孩童的无限关爱与期望,又表达了古人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憧憬和祝愿,故而极受欢迎。随着宋金时期故事题材铜镜的大发展,婴戏主题开始与铜镜艺术相结合并大放异彩,此镜便是其中经典代表,主题纹饰为婴戏图场景,并可细分为三个图景:五童蹴鞠、三童戏车与童子养宠,不仅极具装饰性,更体现了宋时孩童的生活情趣,是对社会文化风尚的直观反映。
“仕女观瀑”人物故事镜
“周穆王吹笛引龙王”故事镜
“仕女梅桩”故事镜
“状元及第”人物故事镜
至殿三回试,蟾宫两度春。
归来何事好,堂上拜双亲。
神仙人物故事镜
“携琴访友”人物故事镜
“王质观棋”故事镜
此镜主题取材于“王质观棋烂柯”的神话传说,据《述异记》载:“信安郡石室山,晋时王质伐木至,见童子数人棋而歌,质因听之。童子以一物与质,如枣核,质含之而不觉饥。俄顷,童子谓曰:"何不去?"质起视,斧柯尽烂,既归,无复时人。”
许由巢父故事镜
许由巢父纹样取材之典故为“巢由洗耳”,关于故事描述最早的文字来自晋.皇甫谧《高士传》:“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并由此延伸而出“饮犊上流”的成语,以示高洁。
许由巢父镜在宋金时期的流行说明此题材所反映的精神内涵符合当时文人雅士的精神追求。“巢由洗耳”的释义为:相传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告诉巢父,巢父批评他没有隐居好才有这样的事,许由懊恼不已,乃以泉水洗耳,说:“向闻贪言,负吾友矣。”之后就隐遁到箕山,后人或谓巢父即许由,故称“巢由洗耳”,并以“巢由”泛指隐者,“洗耳”用来比喻不愿听,不愿问世事。用“巢由洗耳”来表示以杰出尘俗的东西为耻辱,心形旷达于物外。
“巢由洗耳”这一典故之含义激励了许多后来者,他们或学“巢由”隐居不仕;或以之告诫自己保持高尚的志趣与节操;亦或以之体现的廉洁自持之意帮助君主治理国家。“巢由洗耳”在宋金时期铜镜上的应用有多种版式,主题一致然故事背景不同,或于重山间,溪流畔;或是层峦下,小溪旁;亦或是山野深处,苍松之下等等,足见宋时工匠的创造力与铜镜文化的多样性。
转载请注明:http://www.banxiongcaoque.com/btsc/14370.html